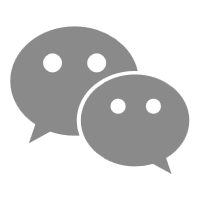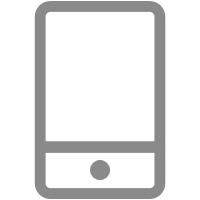迟来的菜心
虽然和老太太住得很近,但一年下来,我四处跑来跑去,和她也碰不上多少回面。所以每年春节的大年三十、初一、“破五”和正月十五,我都尽量和老太太一起过。今年大年初五,我照例回家和老太太一起包顿饺子。
我自认为包饺子手艺精湛,到了老太太那里,我嫌她手慢,自然不需要她动手。不过老太太也没有闲着,一个人在厨房里忙了一小会儿,端出来个解腻的凉菜——拌菜心儿,是我家老爷子喜欢的口味。大白菜直接剥出菜心不用洗,顶刀切“罗锅丝(因为顶刀,白菜帮子都成弯曲的丝,因此被戏称为‘罗锅儿’)”,上边淋点酱油,滴上几滴香油,就这样端上桌,吃的时候用筷子自己拌匀。
这道菜特别简单,看似上不了台面,但在我小时候,这是我家冬季待客最常见的一道菜。我家老爷子性格好,爱交朋友,那时我还小,而他正值中年,印象中,经常有朋友到家里来找他聊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高兴归高兴,留朋友吃饭吃个大事。夏天还好,毕竟物产多一些,西红柿黄瓜容易拼凑上桌,但是到了冬天,家里没有存货,每家每户唯一随时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冬储的大白菜。老爷子待客也很简单,从小厨房里掏一棵大白菜,扒出菜心,不用洗,直接切成罗锅丝堆在盘子里,橱柜里拿出酱油淋上一些,再在上边滴上几滴香油,拌菜心,齐了!酒家里常备着,玲珑、临邛、燕玲春,赶上什么喝什么。一盘白菜心一瓶酒,往我住的小屋的书桌上一摆,一吃一聊就后半夜啦。这样简陋的小菜,在物资匮乏的时代对于朋友就是最大的温暖。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半夜醒过来,桌子上剩着半盘白菜心的场景。直到今天,我心中的菜心就是从大白菜里边扒出来的嫩心儿。老爷子虽然不在了,但拌菜心仍旧是我家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小菜。
改革开放多年,菜市场琳琅满目的南方菜大举进入北方市场实际不过20年。大约2005年前后,北京的菜市场突然热闹起来。卖菜的柜台上多了很多绿叶蔬菜。菜心不是一个部位而是以一个品种开始出现。记得那时候逛菜市场,忽然在小摊上看到菜心,小拇指粗细,长着绽青碧绿的叶子,顶着嫩黄色的小花簇,很惹人爱。价格也不贵,随便几个钱就可以买一些回家,或清炒,或白灼,猛吃了一段时间。
菜心全国各地都可以生长,但北京菜市场里以宁夏产的最多。宁夏近些年除了葡萄酒产业发展快,蔬菜种植也是一样,当地平均海拔1000米上下,适合种植冷凉蔬菜,加上那里光照充足,所以宁夏产的各种蔬菜整体质量颇高,尤其是因为昼夜温差大,吃完后回口略甜。我在上海小住的那段时间常逛菜市场,那里也是将宁夏菜和本地菜摆在一起,貌似当地人更青睐宁夏菜,同样品种的要比当地青菜略贵一筹。
菜心的传统产地在广东。以广州为中心,附近出产连州菜心、从化菜心,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增城的迟菜心。
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几位食客朋友聚会。其中一个家里有广州亲戚的朋友给我搬来一个大纸箱子,一打开,里边是一尺多长、底部有莴笋般粗细的增城迟菜心。这是广东增城特有的品种,因为成熟期比较晚,所以叫作“迟菜心”。正是因为收成较晚,其生长期比一般菜心都长,外形非常粗壮,乍一看它的外表,实在和细嫩的青菜连不上关系。按照外形粗细大小,比照莴笋,我们选了带花的尾巴清炒吃了,其余大多数都被当作废物扔掉了。现在回忆起来,真是老冒进城,没见过世面。
增城迟菜心看着外表粗犷,其实整体都是脆嫩的。广东当地人视为珍宝,比较讲究的吃法是白灼。将迟菜心收拾好,切成20厘米左右的大段;锅里下冷水,先扔进去几段腊肠去去水气,顺便让白水里有一点滋味;然后把整段迟菜心放到水里浸熟,捞出来盛到盘里;把锅里煮好的腊肠切片放到菜上,淋上蒸鱼豉油即可。吃的是迟菜心的鲜甜。
小兄弟阿飞是广东韶关人,家中世代厨师,是标准的烹饪世家出身,十几岁到北京闯荡,在北京开了几家咩都好顺德菜。我找到中意的广东食材,一般都去找他给我加工。迟菜心也不例外。阿飞习惯用猪油渣制作。迟菜心收拾干净后切成段,先用锅略微煸炒一下,出香气备用;锅内下猪油渣,油热后煸炒蒜头,出现焦痕后下菜心,快速翻炒后淋米酒、生抽,加盐找口后出锅。吃油渣混合青菜的香气。
我个人更偏向潮汕炒法。将迟菜心放在案板上,用刀背轻轻拍一下,底下粗壮而空心的部分就碎成大块,上部也会裂开,随即改刀成寸段;将锅底坐猪油,油热后下蒜头煸香,随即下处理好的迟菜心,趁着火热翻炒几下,加上几滴鱼露,迅速翻炒几下直接出锅。因为有了鱼露,咸度和鲜度都有了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己做白灼菜心不会从锅里捞出直接吃,如果条件许可,我会让迟菜心从锅中出来的时候过一下冰水,这样口感会清脆一些。如果在冰水里提前加一些白糖,这样过了冷河的迟菜心吃起来更会格外的甜。

(文 / 霍权 插画 / 郑莉 责任编辑/萧祉默)
本文节选2025年3期《中国烹饪》杂志
欲知详情请移步微店购买当期杂志

欲知详情请移步微店购买当期杂志

版权声明:凡注明“中国烹饪杂志”来源的作品(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未经《中国烹饪》杂志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以及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已经本刊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中国烹饪》杂志”。违反上述声明的,均属侵权,本刊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在此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作者及被采访对象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的立场。
在此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作者及被采访对象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的立场。
相关阅读
北京重庆饭店以厨会友 “麻辣鲜香”破解渝菜标杆魅力
2025-09-24
国务院食安办:加快推进预制菜国家标准制定
2025-09-22
第21届中国火锅产业大会在渝召开,发布多项重磅行业报告
2025-09-22
时光淬炼,清香永恒 | 9月26日,在京城“汾酒之夜”邂逅老酒风华
2025-09-22
哪些抖音达人将成为首批“陈年酒推荐官”?答案即将揭晓!
2025-09-20
北京菜,讲究的就是个“要面儿”!
2025-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