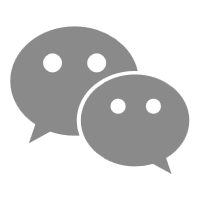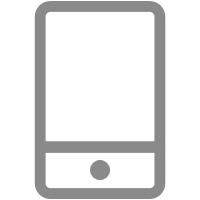鸡鸭鹅蛋,不如黄鳝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甘家口百万庄大街有三三两两的郊区农民在此摆摊卖鸡蛋和豆芽菜,慢慢人越聚越多形成了气候,被当地人称为“自由市场”。
那时候我还小,每天放学后到那里看热闹玩。有天一个铁皮棚子下多了一个人支起一个摊卖鱼,鱼像一条蛇一样细长细长地在盆里,深绿的颜色,肚子是黄的。有人来买鱼,卖鱼的就捞出几条称好分量单放起来,随后拿起一条把头钉在一块长条木板上,用小刀划开肚皮取下鱼骨头,一条圆滚滚的鱼就变成一个扁片了。
一个人买了几条这样的鱼,然后要走了鱼骨,说是熬汤用。我们一帮孩子和卖鱼的都笑了,那个时候即便卖鱼的都不知道拿鱼骨熬汤的道理。
我回家后把这鱼的样子告诉我妈。我妈说:“‘鸡鸭鹅蛋,不如黄鳝’,这是南方人吃的东西。”90年代初的时候,现如今繁华的北京金融街当年还是一片旧平房。在它东侧的太平桥大街按院胡同附近路西,有一座二层楼的小饭馆,因为外边墙上贴着白色瓷砖,所以周围人都管它叫“小白楼”,真正的名字反倒没有人知道了。
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刚上班,每个月连工资带奖金一百多块基本上就交给单位周边各家饭馆了,“小白楼”是其中之一。
一次刚发工资,我又约几个哥们去那里,因为刚“开支”,腰里硬,除了点常吃的几道小菜以外,还加了一道炒鳝糊。那个时代饭馆里一般一道素菜价格3元,像鱼香肉丝之类的肉菜大约5元,一道炒鳝糊,13元!我记得特别清楚。
其他的菜都是服务员负责,唯独炒鳝糊是厨师亲自端上来的。我们酒喝得正在兴头上,一个系着围裙的大胖厨师出现了,左手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是炒好的鳝糊,中间挖了一个坑,里边放着蒜末、白胡椒粉,周边围着一些香菜;右手端着一个小碗,里边盛着小半碗热油。厨师把盘子放在桌子上,把右手碗里的热油当头一浇,“呲啦”一声,白胡椒和蒜末的香气立刻就冲上来了。胖厨师说了一声:“赶紧拌匀了趁热吃。”这大概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堂做”的原始状态吧。我们几个年轻的穷小子哪见过这阵势,看着这菜发愣。那个胖厨师一看,赶紧夺下我的筷子,把鳝糊、蒜末和香菜拌到一起,又把筷子塞回我手里冲我说了一句:“趁热快吃!”扭头就走了。
炒鳝糊出现于1975年出版的《中国菜谱·北京卷》内,去掉围边的香菜,其他一模一样的 ,就是淮扬名菜“响油鳝糊”。鳝鱼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但大都是南味馆子才有鳝鱼菜出品,大概北方人不擅做这种食材吧。京菜擅长“爆”,某名菜馆有一道“爆鳝片”火气十足,此外便没有叫得响的拿手鳝鱼菜了。
老厨师赵宝忠,年轻时在同春园学厨,师从北京淮扬菜泰斗高国禄师傅,学得一手好淮扬菜,做鳝鱼尤其一绝。2007年,我的盛宴雅集美食会第一次活动,赵师傅一道梁锡脆鳝震惊四方。棕红色的鳝丝码放成一座小山,头上顶着黄色的姜丝,虽然整体挂满了糖,但一丝一丝绝不粘连,咬在嘴里像甜酥的小麻花,颜色味道火候均是上乘。后来再也没有吃到那样好的脆鳝了。
几年后的一次活动中,赵师傅又做了一道“紫龙脱袍”。将鳝鱼剥皮切丝,加笋丝炒,是没有酱油的白汁菜,带一点胡椒辣。我说:“这道菜过瘾。”赵师傅说:“这是湖南菜。”
去年我在上海小住,每天早晨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出门坐三站地铁去新泾三村菜市场买菜。菜市场有一个专卖鳝鱼的摊档,一溜好几只大木盆摆在那里,里边是粗细不同、品种不同的鳝鱼。我选细小的笔杆青让摊主处理。摊主捞出鳝鱼称好分量,直接扔到身后的开水桶里,一会儿工夫捞出来,鳝鱼已经开口了,摊主三下两下迅速划下鳝肉交给我。我在旁边摊子上配上茭白毛豆和一点咸肉,回家。
晚饭时分,锅中坐油,油热后葱姜炝锅,下一点儿蒸透了的咸肉煸炒,出香味后再入鳝丝,待炒至弯曲变形后下茭白丝和一把毛豆,烹酱油、花雕酒,稍加一点儿水,加上锅盖焖一下,水分收得差不多的时候撒白胡椒面、蒜泥,翻匀出锅。北方人做菜汁水收得都比较紧,这样香气会更足一些。
南方的食材换成北方的口味和做法,是我处理鳝鱼的不二法宝。

本文节选2024年9期《中国烹饪》杂志
欲知详情请移步微店购买当期杂志
版权声明:凡注明“中国烹饪杂志”来源的作品(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未经《中国烹饪》杂志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以及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已经本刊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中国烹饪》杂志”。违反上述声明的,均属侵权,本刊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在此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作者及被采访对象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