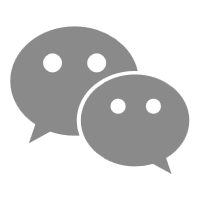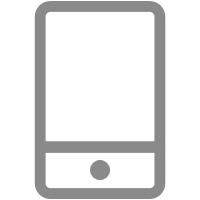宁波炝蟹
苏杭秀丽婉约,到了宁波,山海变得野性,连带着宁波俗语和家常滋味里都有未被驯化的野劲。
形容某人十分开心、敞怀大笑,宁波人说他笑得嘴巴像“虾潺”一样。“虾潺”又称“豆腐鱼”,身子不大嘴巴大,用来形容一个人哈哈大笑时张大嘴巴的样子,非常形象。再如讲某人吊儿郎当,故意懂装不懂,听见装没听见,宁波人称之为“翻白泥螺”。泥螺一般腌后才吃,如果腌得不够咸,又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变质,一变质,壳就发白并上浮。
用“翻白泥螺”形容变“坏”了的某些人,也非常合适。形容做事容易为 “撮虾过酒”,用“气煞鲑鱼”表示生气不说话,以“大水虾射”比喻一个人无主见(虾射是海蜇的别称)。
说起蟹,宁波人的比喻最生动。没有能耐的人被称为“毛蟹”。褪掉了蟹脚的毛蟹,就不能横行了,“看看其长长大大,按落去是褪脚毛蟹一只,没气力哦。”“大蟹弗如小蟹乖,小蟹打洞会转弯”,则用来比喻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年轻人。大蟹打洞只会直着打下去,而小蟹打洞会转个弯,大蟹不如小蟹来得灵活乖巧。就好比现在年轻人起点高,知识面广,本事着实比老一辈的人大得多。听宁波人讲话,喉咙梆梆响,旗帜鲜明,浑厚有力,每句话都带着点海里的鲜味。
一句“红膏炝蟹咸咪咪,压饭榔头就靠伊”,是宁波的孩子自打有记忆开始听得最多的童谣。宁波人说的“压饭”,即下饭的意思。餐桌上出现一盘下饭菜,胃口大开时,自然而然会将菜在米饭上堆满,就像压了一个榔头。一个“压”字,一个“榔头”,形象地概括了宁波人对红膏炝蟹最直观的热爱和推崇。宁波人的蟹,梭子蟹、炝蟹、红膏炝蟹、白蟹、小娘蟹……林林总总,红膏炝蟹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亲朋做客,筵席上摆上了红膏炝蟹,那无疑就是至高礼遇。
宁波人的“炝”,也会被写作“呛”,炝蟹不过火,熟成靠海盐,这是一种独特的生腌方式。关于“炝”的来历,说法有很多,其中一种是:很早以前宁波红膏炝蟹是一道船菜,冬天渔民在海里捕到红膏蟹,偶然有一次海水灌到了船舱里,渔民发现浸了一天的红膏蟹味道特别鲜美,便成了现在的美味;还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的宁波有很多渔民靠捕捞海产为生,他们一出海就是几个月,捕捞到大量海鲜之后往往不能一次性吃完,一位渔民很偶然地将螃蟹放在了盐堆里,发现这样可以将螃蟹一直保存到他们出海回来都不会坏掉,而且被盐包裹的螃蟹有一种独特的风味,于是这种方法就被保留了下来。
宁波靠近东海,所用粗盐即海盐。将整只蟹放在极咸极冻的盐水里泡,水分剥离蒸发,随着白花花的晶体析出的还有凝聚着海洋深处的鲜味,再被蟹肉吸收,仅盐和水,就能成就一道非凡的美味。在外地人看来,生于海里,泡在盐水里,不就是咸吗?然而鲜咸合一,正是宁波味道的精髓。
红膏炝蟹的做法看似简单,梭子蟹背朝下、肚脐朝上放置,拿块大石头压着以免浮上来,盐水一定要没过蟹身,咸淡按个人口味,每个主妇的炝蟹配方都有自己信奉的盐水配比;关键还是选材。渔民们用一生的经验总结出了宝贵心得,捕捞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
霜冻后,螃蟹才开始凝膏,色泽鲜嫩的红膏占据了整只蟹壳,霜降后的第一波红膏蟹膏肥肉厚,是极品中的极品。
待客或小酌时,先把红膏炝蟹冻上一冻,冰冻的炝蟹在半融时切块,让红膏停留在每一块蟹肉上,享用的最佳时机,就是冰霜将化未化之际,鲜味在温暖的口腔中融合,万物回春。(文 / 陶煜 插画 / 郑莉 责任编辑/石叶馨)

本文节选2024年7期《中国烹饪》杂志
欲知详情请移步微店购买当期杂志
版权声明:凡注明“中国烹饪杂志”来源的作品(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未经《中国烹饪》杂志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以及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已经本刊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中国烹饪》杂志”。违反上述声明的,均属侵权,本刊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在此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作者及被采访对象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的立场。